上市材料顯現(xiàn),呷哺呷哺由美林遠東和瑞信(香港)作為聯(lián)席保薦人,所征集的資金將用于新建餐廳以及上海與北京兩地的食物加工廠,經(jīng)過股權(quán)融資和股東借款兩種方式融資不少于1.88億元。
作為“30塊錢吃撐”的小火鍋代表,呷哺呷哺憑仗“一人一鍋”的商業(yè)形式在北京商場站穩(wěn)了腳跟。可是,在近兩年餐飲企業(yè)遍及低迷、上市困難的大環(huán)境下,逆勢而上的呷哺呷哺,尚有北京商場獨大等疑問待解。
沖擊上市正逢“困難時期”
受經(jīng)濟環(huán)境影響,這兩年餐飲業(yè)低迷,商場對全部職業(yè)的成長性、盈余才能和遠景決心缺乏。狗不理、俏江南等均未能完成上市的方針。
近來,呷哺呷哺向港交所遞交了IPO請求。
在呷哺呷哺這次IPO舉動明朗之前,關(guān)于其“預備上市”的風聞就現(xiàn)已甚囂塵上。2013年年末,呷哺呷哺在短短一個月以內(nèi)開設了19家門店,全年開店總數(shù)到達170家,這被坊間解讀為暫時“增肥”突擊上市的節(jié)奏。
本年4月份,有報導稱呷哺呷哺現(xiàn)已發(fā)動赴港IPO,并將于第二季度進行招股。其時這一信息未被呷哺呷哺供認。
事實上,關(guān)于早已火遍京城的呷哺呷哺而言,上市夢已非朝夕。2012年,呷哺呷哺曾無限接近IPO,但終究與資本商場擦肩而過。
2008年,聞名PE組織英聯(lián)出資宣告向呷哺呷哺出資5000萬美元,以超越50%的股份占比獲得了呷哺呷哺的控股權(quán)。緊接著,呷哺呷哺的上市方案正式提上日程,方案當呷哺呷哺店面數(shù)量到達200家時上市;2009年年末,呷哺呷哺斷定,方案將于2012年正式IPO。
到2012年年末,呷哺呷哺旗下門店現(xiàn)已到達330家,但此刻公司與出資方英聯(lián)出資出現(xiàn)了不合:2012年12月,呷哺呷哺對外宣告,原出資人英聯(lián)出資將其所持呷哺呷哺股權(quán)已正式轉(zhuǎn)讓給美國泛大西洋資本集團。
英聯(lián)的退出風波,致使呷哺呷哺未能向港交所及時提交IPO所需的公司內(nèi)部股權(quán)結(jié)構(gòu)材料。這使得呷哺呷哺與榜首次IPO時機坐失良機。
兩年后,呷哺呷哺帶著其從未改動的“一人一鍋”的商業(yè)形式,再次叩響資本商場大門。
“可是這一次IPO也許會比兩年前困難。”一位IPO商場調(diào)查人士通知記者,“受經(jīng)濟環(huán)境影響,這兩年餐飲職業(yè)全部商場都十分低迷,尤其是高端餐飲的全線失敗,也會讓商場對全部職業(yè)的成長性、盈余才能和遠景決心缺乏。狗不理、俏江南都想上市,到當前為止都沒成。”
此外,來自港交所的最新規(guī)則也為呷哺呷哺沖擊IPO帶來了新的壓力。
2013年1月,港交所發(fā)布《香港交易所登載有關(guān)從事餐飲事務的請求人在上市文件中的發(fā)表的指引信》,對追求在港IPO的餐飲企業(yè)發(fā)表文件提出了新要求,包含:供貨商、食材來歷及其報價、“同店銷售額及桌/座流通率”、現(xiàn)金管理、商標、擴大、定價政策以及“食物安全質(zhì)量監(jiān)控及投訴”等方面。
“其中現(xiàn)金管理是很突出的一個疑問,餐飲企業(yè)的財政透明度常常遭到詬病;此外,食物安全疑問簡單發(fā)生危機事情。關(guān)于呷哺呷哺來說,這都是IPO要面臨的難題。”前述IPO商場調(diào)查人士稱。
七成以上營收靠北京
這家由臺灣人開的火鍋店,當前最大的收入依靠北京商場。數(shù)據(jù)顯現(xiàn),北京商場給公司帶來的成績接連三年超越七成。
走在北京街頭,呷哺呷哺的品牌形象很簡單得到辨認。橙色招牌、落地玻璃大窗,常常敞開著的店門,工業(yè)流水線通常的高腳餐位、以及“呷哺呷哺”這一簡單導致獵奇的姓名,都變成呷哺呷哺相關(guān)于其他傳統(tǒng)火鍋店的“特別之處”。
“記不得哪一年開的,我上小學的時分就有呷哺呷哺,其時還覺得很新鮮,如今滿大街都是他家的店”。北京90后女孩陳雙(化名)說,“感覺都快趕上蘭州拉面了。”
公司材料顯現(xiàn),1998年,榜首家“呷哺呷哺”在北京西單倒閉;快到十年后,北京門店數(shù)量到達40家,2011年,呷哺呷哺在全國門店到達170家。
來自呷哺呷哺的財政數(shù)據(jù)顯現(xiàn),到2013年年末,呷哺呷哺在全國的門店數(shù)量到達370家,散布于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蘇、山東等省市。或為合作上市舉動,僅2013年全年擴大門店數(shù)就到達170家,全年均勻算下來,呷哺呷哺每兩天就有一家新店倒閉。
370家門店,假如在全國各個省市渙散規(guī)劃,那么呷哺呷哺的“火鍋王國”可謂地圖廣闊。不過,揭露材料顯現(xiàn),呷哺呷哺僅在北京一個城市的門店數(shù)量就到達247家,比上海、天津及其他區(qū)域商場的門店數(shù)量總和還超出73家。
這家由臺灣人開的火鍋店,當前最大的收入依靠北京商場。數(shù)據(jù)顯現(xiàn),北京商場給公司帶來的成績接連三年超越七成。
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及2014年上半年,北京呷哺呷哺為公司貢獻的營收別離占去公司總營收的87.5%、79%、73.5%和70.7%。
“獨身族”生意異地擴大難
北京西城區(qū)一家呷哺呷哺的效勞生說,在來店的顧客中,一自己前來就餐的占有了多半份額。而疑問在于,在國內(nèi)其他城市,一自己吃火鍋這種需要并不多。
“在北京吃呷哺呷哺,常常要排隊等號,可是去其他城市出差,就發(fā)現(xiàn)呷哺呷哺的生意遠遠不行了,到了飯點兒進店率也不是很高。”一位雪球網(wǎng)出資者表明,這至少能闡明,呷哺呷哺在除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接納程度很低。“北京商場再大,也總有飽滿的一天。小火鍋這種形式如今也不新鮮了,其他品牌正在出現(xiàn)。”
11月19日,工作日的午飯時刻,北京市西城區(qū)一家位于地下一層的呷哺呷哺店內(nèi),等待坐位的顧客現(xiàn)已有七八名。見記者進店,呷哺呷哺店員通知記者“要排號的。”記者看到,店內(nèi)的高腳“吧臺”現(xiàn)已被用餐的顧客占滿,數(shù)名店員繁忙絡繹于吧臺之間供給效勞。一位正在等待的顧客通知記者,自個是一自己來用餐的。“一自己吃火鍋才來呷哺啊,人多的話我就隨便去哪兒了。”
該店一名效勞生通知記者,在來店的顧客中,一自己前來就餐的占有了多半份額,“其次即是兩自己。一群人來吃的也有,不是許多。”效勞生說,也恰是因而,店里設置的多人坐席很少。
“光在北京就開了200家店,這也許是一只牛股!”有出資者在某論壇評論稱,但馬上有更多的出資者對其大潑涼水:“別光看北京,看看別處。”“北京的商場飽滿以后怎么辦?”“在北京的成功可以仿制嗎?”
“我以為呷哺呷哺在北京的成功是有特殊性的。”武漢某品牌征詢公司參謀姜樂樂通知記者,相同的形式移植到其他城市尤其是南邊,就不一定能翻開商場。
“獨自到北京打拼的外地年輕人許多,這些人也許常常都是一自己去吃飯。傳統(tǒng)的火鍋至少需要湊足兩三自己,把單人用餐的客戶掃除在外了,呷哺正巧找準了這個商場需要,一人一鍋,30塊錢就能吃好。”姜樂樂說,“在國內(nèi)其他城市,一自己吃火鍋這種需要并不多。”
“別的,假如呷哺到了南邊,它的快餐式火鍋是很難滿意南邊人對飲食口味的挑剔的。”她說,“據(jù)我了解,許多吃過呷哺呷哺的武漢人都覺得他在口味上毫無特點。”
“呷哺呷哺當前的營收主要依靠北京這個商場。但這一個商場的容量終究是有限的。如今呷哺該占的商圈都現(xiàn)已根本占據(jù),后續(xù)必定還要擴大,可是怎么擴大、往哪里擴大?都有疑問”。前述IPO調(diào)查人士以為,“呷哺將來不得不繼續(xù)走出北京,可是走出北京以后,能不能活得滋潤即是疑問了。”他表明,北京商場的成功不代表呷哺呷哺可以在全國仿制這種成功。
與火急沖擊資本商場的呷哺呷哺比較,相同面臨上市的引誘,呷哺呷哺的同業(yè)“老大哥”海底撈體現(xiàn)得適當抑制:董事長張勇曾表明有方案將海底撈上市,但并未斷定在何處上市。
張勇以為,當前并不是上市的最好時刻,“等商業(yè)形式可以盈余并可以更輕松地仿制后,海底撈才會上市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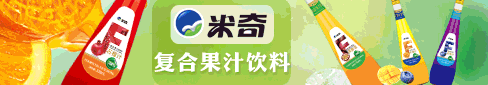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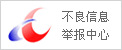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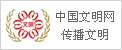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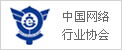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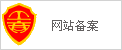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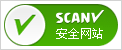 CopyRight ? 2013-2022 Brand food.cn All Rights Reserved.
CopyRight ? 2013-2022 Brand food.cn All Rights Reserved.